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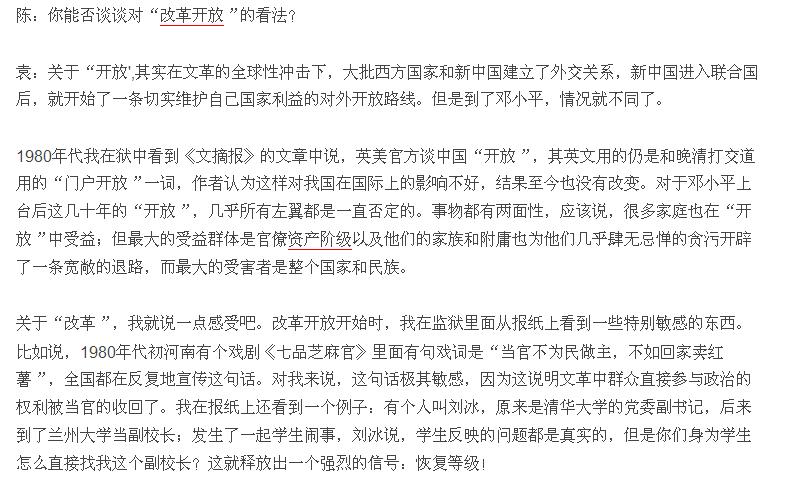
袁老先生还是“犹抱琵琶,半遮面”地不肯说出来,在1976年10月6日和30多年“改开”后现在中国社会的真实性质。他回避一个客观事实既资本主义已经彻彻底底在中国复辟了。
袁老先生能在和谐时代里各地“游学”式的讲道,他是在宣传马列毛科学真理的真谛么?
毛主席说:“他们对文革不理解,对文革有怨气;但有怨气,不要撒向人民群众啊。”(这里“他们”是指的反对文革的那些“老革命”和“老干部”。)通过30多年“改开”的客观事实,毛主席当年的科学预见确实是被历史验证了。
在和谐时代里大谈什么所谓“纯粹民主”、“一般民主”,而避谈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。要么是刚初出茅庐地新手,要么是老谋深算地披着羊皮的狈。
在和谐时代里的某些人,又拾起野阪参三的牙慧。(其鼓吹“民主共同战线”)